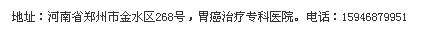第八章情感性疾患
动力取向精神医学已经体认到,情感性疾患很大程度上会受到遗传与其他生物因素的影响。事实上,要研究遗传与环境如何互动进而产生精神疾病,忧郁症可以当作一个理想的模型,目前已知的是,单极性忧郁症约有40%可以归责于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则占了另外60%左右的成因。
肯德勒和他的同仁们为了建立忧郁症的致病模型,追踪了对女性的双胞胎配对,其中有些是同卵双生,有些则是异卵双生,结果发现遗传因素的影响尽管显著,却不是那样绝对。该研究中最有力的预测因子为近期内的压力事件,其他如人际关系与气质(temperament)上的神经质(neuroticism)倾向,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其中后者似乎会使许多个案失去社会支持的力量。
在后续的研究中,肯德勒等人扩大双胞胎研究的个案数,而有了进一步的发现,其中最有趣的莫过于:个案对压力事件的易感性亦为遗传因素所控制。举例来说,一群遗传上危险因素较少的个案在没有压力事件发生的状态下,每个月发生忧郁症的机率大约是0.5%,如果暴露到压力事件之中,发生率则会升高至6.2%;然而与遗传上的高危险群相较,两者之间有显著的差异,后者在缺少压力事件的情况下每月的忧郁症发生率为1.1%,压力事件存在时则升高到14.6%。
纽西兰一个收案数达名孩童的追踪研究,也支持了上述的致病理论模型。研究者发现血清素转运子基因(5HTT)上的启动子(promoter)区域,可以透过功能多样性来调控压力事件对于忧郁症的诱发能力。
在后续分析里,肯德勒等人又发现压力事件与忧郁症发作的关连性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比例并不具有因果关系,因为有些容易发生忧郁症的人其实算是自投罗网,自己跳进高危险的环境中,像前面提过的神经质倾向者即是一例,他们很容易就将自己与他人隔绝而孤立起来,把重要关系给搞砸了。在这个研究里,最大的压力源包括至亲的死亡、受到侵犯、严重的婚姻问题、离婚或分手等,除此之外,也有若干证据显示早年受虐、疏于照管或分离等事件,也会造成某种神经生物学上的易感性,使得个案成年之后面对压力事件时比较容易产生忧郁反应。肯德勒等人稍早的研究发现,童年或青少年时期曾经历与父母分离的妇女得到忧郁症的危险性也会升高。最后这个团队的研究也注意到,压力事件对忧郁症的影响有性别差异,男性比较容易被离婚、分居或工作上的问题所影响,女性则比较难应付周边人际关系问题所产生的压力。
如同尼莫洛夫所指出的,佛洛伊德有关早期失落(earlyloss)会使人变得比较脆弱、比较容易产生忧郁症的说法,已经在近期的研究中获得证实。阿基德等人做过一个病例对照(case-conrrol)研究,找来一群症状不一的成人精神病患,评佑他们在十七岁以前由于父母亡故或永久分离等因素而失去父母亲的比例,结果发现童年失去父母亲这件事显著提高了成年后得到忧郁症的机率,其中因为永久分离而失去父母的,甚至比父母亲亡故带来的影响还要大。此外,事件发生的时间早晚也和后续的影响力有关,九岁以前发生和九岁之后发生相较之下,亦有较高的致病风险。同样地,吉曼等人也发现,童年早期父母离异与终身的忧郁症发生率之增加有关连性。事实上,会引发忧郁症的不仅是童年的失落而己,身体或性方面的虐待也都曾经在研究中被证实与女性成年之后的忧郁症有关。其他相关的研究还包括:童年曾经被虐待或疏于照管的女性和未曾有此不幸经历的女性相比,成年后苦于负向人际关系与低自尊的比例高达两倍之多,而这些个案中发生忧郁症的比例更比对照组高出十倍。
这些与成年期忧郁症相关的早期创伤似乎能够在个案身上造成若干永久的体质性改变,伟思林安等人发现童年受虐的忧郁症妇女,其左侧海马回(hippocampus)的平均容积,比起未受虐的忧郁症妇女和健康个案来说,分别要小了18%及15%之多。此外有不少研究也都发现,肾上腺皮质激素促泌素(CRF)能刺激脑下垂体分泌肾上腺皮质素(ACTH),这种激素在忧郁症个案之脑脊髓液中的浓度较对照组为高;此外,倘若把肾上腺皮质激素促泌素直接打入实验动物的脑中,这些动物便会出现若干与人类的忧郁症颇类似的行为表现。上述的研究成果提示我们,情感性疾患的“压力-体质模式”(stress-diamesismodel),也就是说存在有某种由遗传因素来决定的基质(substrate),可以使得突触(synapse)间的单胺类(monoamine)传导物质减少,或是使下视丘-脑下垂体-肾上腺轴线对压力的反应性增强;在没有严重压力存在的情况下,由于没有超过遗传所决定的阈值,并不会引发忧郁,然而被虐待或疏于照管的经验可能会活化压力反应,使得肾上腺皮质促泌素细神经元的活动量增加。如同前面说过的,这些细胞对于压力有很敏感的反应,在忧郁症患者身上更是如此;某些个案身上的这类细胞甚至会变得超级敏感,即使只是很小的压力,也会引起极大的反应,海曼等人也发现到,童年的不幸事件似乎让成年的妇女个案很容易在遇到压力时产生忧郁症的反应。
在一个设计精良的研究里,黑曼等人找来49位年龄介于十八到四十五岁之间,没有服用任何精神科或贺尔蒙类药物的健康女性,把她们分成以下四组:一、没有童年被虐待或精神科的病史;二、目前处于忧郁症中,童年有遭受性虐待或身体虐待的病史;三、目前没有忧郁症,但童年时曾经遭受过性或身体方面的虐待;四、目前处于忧郁症状中,但没有童年受虐的经验。在这项研究里,有创伤历史的个案无论在脑下垂体、肾上腺或自主神经系统方面对压力的反应都要比对照组来得大,这种效应在目前有忧郁或焦虑症状的个案身上尤其明显,比方说上面的第二组个案,其肾上腺皮质激素对压力的反应竟是对照组的六倍之多;最后研究者下了这样的结论;孩童时期被虐的经验可能会造成肾上腺皮质激素促泌素的分泌减少,产生下视丘-脑下垂体-肾上腺轴线以及自主神经系统的过度反应,这些生理反应似乎和忧郁症有关。
由于精神动力模式将成年的精神病理现象归因于早年的创伤,童年时期的压力事件原本就是考虑的重点,然而在此之外,动力观点更是强调压力事件所蕴含的意义。临床工作者得要常常提醒自己,有些事情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不过尔尔,却因为个案意识或无意识中蕴藏着深刻的意义,而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海曼也提到:“在这个领域中研究者已经达成共识,重要的不只是负面生活事件的发生,还包括个人对事件的诠释,以及相关脉络下该事件所具有的意义。”在一个长期的追踪研究中,海曼等人发现如果压力源的内容与个案的自我定位(self-definition)相关,更容易引发忧郁症;换句话说,对于以社会关连性(socialconnectedness)来定位自我的个案来说,重要人际关系的丧失会比较容易诱发忧郁症。相反地,如果个案重视的是个人的支配与成就,一旦经历到工作或学业上的失败,会比较容易产生忧郁症的反应。
肯勒德等人最近一个研究是从弗吉尼亚州双胞胎档案来找个案,他们发现带有个人特殊意义的生活事件和忧郁症的关连性更加密切,在访谈中研究人员发现,从事件带来的失落与受辱(humiliation)程度可以预测忧郁症的发生,其中同时具有受辱(由于重要他者主动要求分离而引发的羞辱)与失落这两种意义的,和单只带有失落的比起来,产生忧郁症的比例较高,而直接羞辱、贬损个案的事件与忧郁症间亦有相当高的关连性。由此可知,动力取向的治疗者必须要去探讨压力事件的意义,才能更精确地掌握事件对个案所带来的独特影响。
忧郁症之精神动力学理解
精神分析或者精神动力学派对忧郁症的概念可以追溯自佛洛伊德的经典之作《哀悼与忧郁》,其中的核心概念便是早年的失落会造成一种易感性,使得成年之后较容易产生忧郁症。他也注意到忧郁症个案常见的自我诋毁,是由于转而向内的愤怒,他甚至更精确地指出,愤怒转向自己的原因来自于自我对失落客体的认同作用,他是这么说的:“因此客体的阴影笼罩在自我之上,以致自我被某个特殊的内在动源(agency)所评断,就好比自我也成了某个客体,亦即那个失落的客体。”年佛洛伊德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将失落的客体内化并加以认同,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是放下生命中重要他者的唯一方式,同年出版的作品《自我与本我》中,他提出这样的推论,忧郁症患者往往拥有相当严厉的超我(severesuperego),这是由于他们对于自己曾向深爱的他人表现出攻击性而感到愧疚不已。
卡尔?亚伯拉罕进一步延伸佛洛伊德的想法,把现在与过去之间连接起来。他认为,罹患忧郁症的成人在童年时期自尊曾遭受强烈的打击,面对过去或当下这些伤害自己的人(因为对方不爱自己了,或因主观认定对方不爱自己了,而受到伤害),现下的失落或失望会引发患者对于这些人强烈的负面感受。
克莱恩则谈到面对痛苦失落时所产生的躁式防卫(manicdefense),比方说自以为无所不能、否认、轻蔑、理想化等,这些防卫机制使得我们可以:一、拯救与修复失去的所爱;二、拒斥坏的内在客体;三、否认自己对所爱客体卑下的依赖。临床上个案可能以下面几种方式来展现这种防卫机制:否认自己对于他人的攻击性、呈现出与现实情境不搭调的溢乐感、对别人过度理想化,或者表现出苛刻、不屑他人的态度,以否认自己对于关系的需求;在这种自我膨胀的躁式防卫中包藏着一种意图凌驾于父母之上、翻转亲子关系的冀望,这样的欲求可能反过头来产生罪恶感与忧郁,克莱恩以此来解释为何忧郁经常会在成功或晋升之后发生。
克莱恩的阐述可以帮助临床工作者理解到,在生物性因素之外,躁症同时也可以有心理观点的解释。自我膨胀的躁式防卫作为一种防卫机制的功能,在不悦型躁症(dysphoricmania)的患者身上看得最清楚,在这种状况下,焦虑与忧郁浮现于躁症发作之上,进而需要更强大的躁狂来否认。除此之外,轻躁也经常被拿来作为对抗忧郁情绪或哀悼反应的防卫手段,举个例子来说,有个病人在得知母亲的死讯之后反而觉得快活,他觉得自己变得有力量、快活,从依赖中被解放出来。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情绪,他仍能注意到,自己没有悲痛欲绝是很奇怪的事。
五十年代时比布尔提出了与佛洛伊德和克莱恩都大相径庭的看法,不若上述两人把忧郁当作是攻击性转而向内的结果,他将忧郁视为一种原发性的情感样态(primaryaffectivestate),来自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拉锯。他指出人有三种自恋性的企求:期望自己值得被爱、期望强大与优越,以及期望自己够好且慈爱,这三种期待被当作言行举止的标准,然而自我同时也在想象或现实中认知到自己无法达到这些标准,忧郁于焉而生,这便是忧郁症患者感觉到无助、无能的缘由。他认为任何自尊的伤口都会产生忧郁,由此可知自恋的易感性对比布尔来说是了解忧郁症何以产生之钥,在他的理解中,超我并不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
在研究了许多忧郁症孩童的病历纪录之后,医院的山德勒与乔菲作了这样的结论,当孩子的自尊有了严重的失落,同时又无能复原的时候,便会产生忧郁。他们强调失落的不只包含现实或想象中的所爱,也包括客体所带来的一种安适状态(stateofwellbeing),即使这种状态是如此地遥不可及,它仍旧不断地被理想化与渴望,就像是“失乐园”(pararuselost)一样。
贾克森以佛洛伊德的阐释为基础,进一步指出,尽管没有表现得一模一样,忧郁的个案大致上看起来仍像极了那个无价值感、失落的客体一般,于是到头来这个坏的内在客体——或者说是失落的外在客体,转而成为残虐的超我(sadisticsuperego),忧郁症个案于是成为“超我的受害者,就好像被残暴的双亲凌虐的小孩子一样无助。”
I太太是一位四十九岁的家庭主妇,她最近得到了精神病性的忧郁症(psychoticdepression),她深信自己一文不值,而且不断回想父亲曾经把她打得多么惨,就因为她是个“坏女孩”。每当这个施暴的父亲的内射体融入她的自我观里,她便割伤自己,这么做一方面是一种自我惩罚,另一方面也是对这个内射体发动攻击;其他时候,父亲则是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内在客体,或者化身为不断斥责她的残虐超我,在这种情况下,I小姐的幻听包括了“你很坏”、“你该死”等责骂声。
透过I小姐的内在客体世界,我们可以窥见,在精神病性的忧郁之中,一方面自己可能与客体融合,另一方面也重新启动了一组内在客体关系,其中残虐的坏客体或原始的超我,迫害着坏的自我。贾克森认为躁症的自我膨胀可以理解成自我与超我两者奇妙的融合体,使得原本严厉、暴虐的超我摇身一变,成为慈爱与宽恕的形象,当这个理想化的客体被投射到外在世界,过度理想化的关系也随之产生,此时,攻击性与破坏性从而被否认掉。
艾瑞堤从临床经验中作出这样的推论,他认为严重忧郁症患者病前往往抱持着某种特殊的信念,特别是一种不为自己、只为别人而活的信念,他将这个关系里的别人称作支配性的他者(dominantother),比方配偶便经常扮演这样的角色;其他时候这个位置也可以被某种理想或某个团体来取代,当占据这个宰制地位的变成某个超越性的目标时,艾端堤称之为支配性的目标(dominantgoal)或支配性的原因(dominantetiology)。在这样的关系里,即使这些人感觉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也没有办法改变或停止这么做,最后他们可能会相信,如果没有办法从对方那种得到期待的反应,或是不能达成那个无法企及的目标,生命就好像失去了价值。
依附理论亦有助于我们对忧郁症的理解。约翰?鲍比认为孩童对母亲的依附为存活所必须,倘若这种关系因为失去母亲而遭到破坏,或是关系无法保持稳定,孩子便会觉得自己不值得爱,觉得母亲或照顾者靠不住,因而把自己给抛弃,等到他长大后遭遇到失落,这些感觉便会被再度活化,因而进入忧郁状态中。
表8-1历史上对于忧郁症/轻郁症之精神动力理论模型的重要论述者
佛洛伊德
转而向内的愤怒
亚伯拉罕
当前的失落活化了童年时期自尊所受过的打击
克莱恩
处于忧郁位态时发展上的挫败
比布尔
自我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拉锯
山德勒与乔菲
对于童年时期真实存在过或是幻想中的失落所作出的无助反应
鲍比
失落活化了来自于不安全的依附关系中不被爱与被抛弃的感觉
贾克森
失落的所爱转而变成严厉的超我
艾瑞堤
为了某个支配性的他者而活
忧郁症的精神动力理解中有许多常见的主题,读者可以参阅表8-1所做的整理。大多数的精神分析文献都强调自恋的易感性或脆弱的自尊,愤怒与攻击性也在许多理论中占了重要的分量,尤其是着墨于这两者所滋生的罪恶感与自我贬抑上。此外,有些人忧郁的成因,则是试图寻找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理想照顾者,有些人则为严厉与完美主义的超我所压迫与折磨。有时,这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由于想要扳回一城,个案可能会过度理想化自己或某个重要他者,然而理想化的后果往往是带来更惨痛的失望,引发更严重的忧郁,反而令个案贬低自己的价值,将更多的愤怒导向自己。
当代的动力精神医学已经认知到,早年的创伤经验会使孩童发展出一些造成困扰的自体或客体表征。以身体或性方面受过虐待的个案为例,受害的孩童将罪有应得、该当受虐的坏自体给内化,对于可能受害时时刻刻保持警觉,此时的客体表征就如同一个严厉而残虐的角色一般,不断地攻击自己,这种被内在的施虐性客体所折磨与迫害的感受,也和临床上所见的严酷超我现象吻合;相似地,早年失去父母的孩子内化了被遗弃的自体,这个自体的需求无法如一般人那样被双亲所满足,伴随着这个自体一起内化进来的,还包括那个弃人于不顾的客体表征,这样的小孩便在失落与期盼的交揉混杂中成长,日后一旦遭遇到有关失落的压力事件,旧有的关系便很容易再度活化,产生放大效应。此外,由于孩童的自尊与幼时如何被对待息息相关,经验过失落与创伤的孩子,自尊往往也格外脆弱,因此,此种情境下孩子与父母或其他重要他人的关系可谓问题重重,而所型塑出来的人格于成年之后往往也会在人际关系上遭遇困难,例如无法和别人建立或维持一段关系,或是比较容易遭遇失落的打击和自恋性创伤。
有关防卫机制的研究也是动力精神医学相当重要的部分,防卫机制往往是在童年时期处理痛苦情绪当中逐渐成形的,凯翁指出,某些防卫机制可能会导致忧郁症的生成,但有些则具有保护效果。敌视自己,亦即过度地或持续地自我批判,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不成熟的心理作用会助长负面归因的风格,进而促进忧郁的产生。其他不成熟的防卫机制也会增加忧郁症或其他精神疾病的发生机率。反之,一些比较高阶的防卫机制,譬如原则化,又称为理智化,也就是利用一般或抽象性原则重新诠释现实,则有正面的效果。由此可知,防卫机制的动力取向式理解对于忧郁症的处置有极大的帮助。
另一个大家必须谨记在心的原则是:动力精神医学向来重视每个个案的独特面,而非只把个案当作某个标签下的一分子,因此我们对于个案的防卫机制与客体关系必须个别考虑。举个例子来说,布莱特在他的忧郁症个案中,发现两种潜藏的精神动力结构,其中的依附型经常有无助、孤独的感觉,或是因为害怕被拒绝或失去保护而觉得自己很脆弱,这一类的人往往期望能获得照料、保护以及爱,他们很容易因为失去人际关系而受伤害,否认、拒斥、置换与潜抑是他们惯常使用的防卫机制;相反地,另一种内射型的忧郁个案主要北京哪家医院治白癜风比较见效北京白癜风专业的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