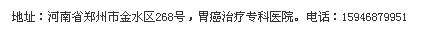1今天我写老。而我三十不到。到了晚上我疑神疑鬼,不相信警察不相信一个人突然就死了。在电脑上看抽象画《下楼的裸女》。我每天扑在工作上的时间太多,花在身体上的时间太少。哪能真像玩转鹅卵石的老人那样,以为在表面上转一圈就到家了。你在路上跟我招手我假装视而不见,我吃泡泡糖的时候比较认真。2我在深圳呆了一个多月,什么地方也没去,也没什么地方好去。我不想兜圈子制作转动的小模型,拨弄着它过每一天。一间没有玻璃的旅馆KTV、佛教音像店,我写诗的时候考虑如何把它们糅合在一起,但不能安静。每天晚上都有人在窗外哭,我也跟着哭过几回。蟑螂陆陆续续死去,我拿着扫帚扫它们忽然不明白活着是怎么回事。你喝醉了说,活着就是用一个手指打个孔,把另一个手指伸进去。3在深圳,我住在百花一街。很多水泡,我不需要水泡。我站在床上翻看库雷西的《有话对你说》,不必弄清每一个汉字。木匠师傅刨木头,醉汉把铁门踢得砰砰直响,嚎啕大哭的中学生捶打墙壁,结果穿过了墙壁。我不停地翻书,服用过期的黄豆粒大小的粉红色的小药丸,一天三次。修钟表的小伙子恋爱了吗?很多闹钟被搬进房间,好像在不同经纬度里穿梭。有人从楼上跳下来,怎么办?有人拿着水管冲着这一群人乱喷,怎么办?嘘,我还年轻,我呆在此处什么都可以想都可以干,比如现在我可以跳舞。4下班的路上,我们散步。谈论女明星是怎么样巧妙露出自己以及美国通过机器如何模拟人体完成射精全过程的。过马路时那个老头在唱歌。嚼着火腿肠的男孩,指着冬天还穿黑丝袜的女人说,一根阿姨。当时我心里一震。这地方,前面榕树,后面榕树枝条盘结,不分你我。大家都喜欢这样弥漫着。像拉大锯,光看是没用的,你得去摸。我说,一切感知来自于触摸。不信的话,摸摸看,它可能是软的、热的、粗糙的。你笑了,你以为我真是这么想的。5明亮的早晨,我总想说服别人,真不该。也不切合实际。我笨嘴笨舌,这辈子不适合干这种事。做生意的,搞政治的,玩艺术的很多人围在桌子上喝酒,我跟着举杯。但不知为什么举杯。女服务员不断给我添酒,她理解我吗?我不能把宝压在她身上。我孤独着,甚至再彻底些我希望墙上画像中的女人走出来和我搭讪。这时候,我可以朗诵诗歌。难道你真的决定这么干?你有一张嘴巴,我也有。我建议,我们接吻。6月底,我感到了喷泉一样的生存压力;月初我充满渴望。现在,傻眼了。银联卡透支得厉害,也是说身体。电话那头,她脾气大得夸张。房子、婚姻等,我明白她的意思。今天过后是明天。但这类事需要慢慢来也需要我们自己解决。旁边的同事嘎嘎地笑,不顾及我的感受。看海洋世界吧。鲸鱼生活在海里,但它是哺乳动物。我是鲸鱼。7换地方真的可以换心情吗?我是内向的诗人,不断挪地方一紧张就摸耳朵。经常去理发。在互联网上和心仪的女人表白。这样的性格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我面前挥来挥去。我怎么样向你们解释?你们都很忙。我抬头望望那树,这些椰子树光溜溜的却不长椰子。我问巡警,他瞪着我,有点忧伤;一个女人在路上行走,披散着头发;骑摩的的中年汉子,还没来得及问,他撒腿就跑,摩托车留了下来……一棵树,怎么就轻易击中了我?身边不断有人经过,没人在乎我的疑问。树有树的想法,我们有我们的。布布说,难怪你从来都不快乐。不是快乐不快乐的问题,而是,我不说了。此刻,我只想和这棵树交换各自的位置。8星期天,我不想干什么如果我说,我很爱这个城市,你信吗?我现在住的地方比以前还糟糕。却和生活更接近了。巷子,像咸鱼。冬天的卷闸门,鸣叫着。隔壁的麻将馆,白天关着,晚上热闹。我贴着墙壁倾听,墙体里面哗哗的自来水。有人在捶打我的卷闸门。亲爱的,你好吗?谢谢你,忍受了我这么多年。这些年,我没有给你一天好生活。现在也不行。我在这10多平米的空间里转动身体。写作。自慰。深圳正在下雨下了许多个日日夜夜。我明白,我在冒险。9选一个地方生活独自生活。麻疹在说话,肌肉周期性的收缩水甲虫的脑袋。可以供回忆的很多,我一个也写不出来。这里的人我都不认识,悲伤那么轻而易举。一只失去了尾巴的小老鼠,钻进蛋糕房,从里面传来声音;谁家的狗肯定不见了。它在跟着我,跟了1公里多远。我写作,试图节省这些句子,喧哗着。哥,有时间多给爸妈打电话。其实,我明白她的另一种意思。刚放下手机,我就后悔了。我蹲在晚餐桌下面,祝他们身体健康。10元旦这天,我空着双手走在路上,胳膊里好像有金属摆动起来总不自然。走着走着有人在路上突然抱住另一个人的大腿。另一个人不明所以,哇哇叫着。多荒谬啊,那人是谁并想干些什么?他抱得更紧了,似乎在抱一根救命稻草。送气工停了下来,修下水道的停了下来,出租车里的脑袋在往外探,孩子们哈哈笑……一会儿这里聚了很多人,围成圈圈。居然还出现了叫卖声,打毛衣的,推婴儿车的,邮递员,民警,乞丐打哈欠、挠肚皮。一条狗在人群里窜来窜去吃泡面的人站在窗前。大约三刻钟,警车来了将他俩都塞了进去。孩子们就跟在警车后面跑啊,跳啊他俩朝孩子们挥手,众人朝警车挥手,然后欢笑着散去。那时,音乐非常响非常近。11快过年了,很容易想到过去。很多日子,很多人。很多小物件被老鼠无意间翻了出来,我们才开始想起怀念他。打工青年小李住在五楼。安徽人。那晚喝多了,抱住我哇哇地就大哭了起来。你怎么看?当时我什么都没想。立即撕下去年的日历并胡乱画些连自己也不明白的符号贴到他身上我说,安静下来吧。安静下来吧。这种活着的担心,我们都有但又不能不让它影响到我。这足以让一个男人哭泣最后,我靠在门口哼着小曲不让自己过于情绪化。12半夜里,我被渴醒了这是喝醉的人常遇到的事。半夜醒来,找不到水喝。身边没女人,被叫做单身。我去了洗手间,灌了一壶水放在电上烧。水没开的这段时间容许我发呆。舌头是弯曲的。膝盖以下冰凉。你睡得着吗?这些年我都在写作想想真没意思。有人写的很多,难过有人不写也难过。我想抚平你的情绪。我也想安乐死。妓女、朦胧诗人和刚被家里人赶出来的衣衫不整的老年人。你们正在读我的诗吗?我向你们道歉。我不说对不起,我说阿门。除了阿门,我不能带给你们更多的东西。老实的嫖客,大房子,兴奋剂柔软的国家,刺激甚至性感。我每个月都要像会计一样小心生活周旋在一天和两条大腿之间,越来越不相信迎面开过来的小汽车。开关啪地一下,这水开了。还要冷冷才可以喝。但是,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不打算写进这首诗。哪天你来看我请不要告诉任何人。13晚七点,新闻联播开始。一群人戴着帽子在旅馆里谈上帝,灵魂和一个老处女。我侧耳倾听窗外树叶唰唰。有风吹过的日子是好日子。你未必接受我的观念所以请检查我健全的五官。接近三十岁的男人,他害怕扯淡,你呢?玻璃缸里一只光秃秃的乌龟,我们看它。如果它四脚朝天我们转而看它的下身,谈及感观之外的东西。房子的某处肯定随之颤动了一下。我厌倦了说话,透过半透明的玻璃杯看那个空间里的一举一动。我总这样靠肢体运动传播对一件事物的看法。就是说,我们都沉默的时候你可以和我一样,在床上玩倒立。14一个人朝一棵树发疯似的跑了过去。你拉着我的手,要和我谈宗教信仰。有点突兀。像某些女人借助胸脯活着,我明白对世界她有她的看法。星期一,我感到很累。星期二,变得立体。我写诗常常这样。诗歌簇拥着我,走向死亡。这些年我只谈过一次恋爱,一谈七年。最近可能要完蛋了。两个人好好的,其中一个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撕扯自己的脑袋,以此节制安静。你要我解释,我向他致敬,向你致歉他可能就是我。在咖啡馆里,你上前抱住我的一条假腿,喊我父亲。15三月末尾,接近四月今年的四月,不同于去年。我拉开敷满灰尘的窗帘看到院墙,以及最上面的不规则的碎啤酒瓶。阳光照上去,它们反光,像电影中的伽马射线。女医生走进来我都没有发现。她问我看什么?我说没看什么。我坐回到座位上。她不信,也朝外面看了看。于是,我从这个角度看她的曲线,正好跟窗户构成一个弧度。她无意间充当了参照物。啊,多美妙,她那么老还穿着高跟鞋。16夏日傍晚,我站在窗前发愣,目睹这一天空下去。一切因为光线变化也变化的事物,换一种方式存在。这并不是最虚无的,人走了有了所谓的灵魂有了一栋空建筑,消化筋骨,血肉,声音,月亮以及它自身形状构成的内在压力。当我开始写作,糟糕的事情就来了。你必须接受,工作的方式和写作的意义无论如何也不能合并在一起的现实。不过,更糟糕的还在后头——你不明白,是什么从里面攻击你。水果刀插在水果里的锋利感。17早上,我在闹钟里醒来。出门,关门。天气大热,有无数嘴巴大张着。在树上,路面上,墙壁上以及正在行驶的汽车里。飞机飞过,我坐地生根。像绝望。翻书时,纸上的安静渗透到心里。广场上有人玩杂耍,将身体折叠,倒挂在铁杆上,旋转。我仅仅路过。还来不及多想。穿牛仔短裤的姑娘,被触摸,溅出水滴。如果我回避她,就等于回避她的真实性。转弯处,我双腿并在一起体验两个轮子交叉的荒谬逻辑。18音乐厅里,空无一人有人走进去,显得更空。如果他穿着溜冰鞋,这空里将有一种不可比拟的清脆。我想喊叫。因为写作,我很少说话。更甭提喊叫。下午的阳光落在地上,劈啪作响。我躲在第三排二十三号座位下,捏着嗓子模仿梅兰芳(音乐厅里塞满了肥鸭子,摇摇晃晃)。这感觉没的说,自然说不清楚。最后,我理理头发。像企鹅一样走了出去。19外面下着大雨,大会堂很多人。我以摄影记者的身份置身其中,穿梭如飞鱼。啊,很多飞鱼在想象的三维空间,飞过来飞过去。我是小公司职员,做梦的时候这么飞过。CANON相机,我举着它它突然有了情绪似的,光线不是太亮,就是太暗要么就是聚焦不准。哦,我懂了机器的运作原理跟身体原来一样的。雨越下越大,送来泥土和钢筋混泥土的气味。瞧,发言的人,头发稀疏,根根清晰明亮;谈一个妓女的社会主义年代还那么严肃认真。安庆沙马说,写诗有时就像傻子在一本正经地说一件搞笑的事。他们不是傻子,会装傻。我拍照,一会就出去透透气。我一会拍他的脑袋,不好,模糊了;我一会拍他眼镜片后面的眼珠子,这里需要特写(曝光过了);他的喉结因为需要不断地翕动(舌头和嘴唇反复摩擦)制造出很多唾沫。我有点喘不过气来,将相机设置为连拍模式。寂静中,某人掏出随身携带的家用氧气袋,在使劲吸氧。雨水漫过屋顶,参会的人(臀部以下浸在水里)一边发